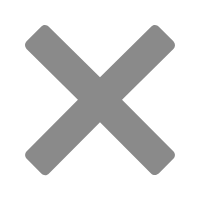-
结婚纪念日当天,我发现恩爱丈夫是小偷
第二章
我不知道在冰冷的地板上坐了多久,直到窗外的天光泛起鱼肚白。
我擦干眼泪,将一切恢复原样,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。
陆景琛回来那天,带回了他从欧洲拍到的一幅古典油画,兴冲冲地挂在客厅。
他从背后拥住我,下巴抵在我肩上,语气是惯常的温柔。
“喜欢吗?我们的家,就该被这些美好的东西填满。”
我看着镜子里他那张英俊儒雅的脸,胃里一阵翻涌。
美好?
这个用走私国宝换来的“家”,每一寸都沾着肮脏的铜臭。
“景琛,我觉得有点累。”我挣开他的怀抱,声音平静。
寄居在我家的白诗雅,陆景琛那青梅竹马的“初恋”,适时地端着一碗燕窝从厨房出来。
她一年前因为一场“意外”失忆,陆景琛便把这个“无依无靠的可怜人”接回了家。
现在看来,这场失忆,恐怕也和那些翡翠的“来源不明”一样,干净不到哪里去。
“瑾年姐姐脸色怎么这么差?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”她走到陆景琛身边,关切地看着我,姿态亲昵得仿佛她才是这里的女主人。
“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。”我懒得看她,径直走向沙发。
“就是你太拼了。”陆景琛接过白诗雅手里的燕窝,坐到我身边,自然地拿起勺子,“我最近又收到了一批好东西,本来想让你帮我掌掌眼,既然累了,就先算了。”
他永远这样。
体贴,尊重,从不强迫。
可那句“好东西”,此刻在我听来,就是一句催命符。
又有一批国宝,要经我的手,流落在外了。
我看着他递到嘴边的勺子,心里盘算着。
报警?证据不足。他的所有交易都通过代理人,资金流向也干净得可怕。这份报告,他完全可以抵赖是伪造的。
摊牌?他会立刻销毁一切,甚至将我灭口。
一个能布局三年的男人,心有多狠,我不敢想。
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我不仅要让他付出代价,还要把那些被我“送”出去的国宝,一件一件地追回来。
这是我的赎罪。
想到这里,我抬起头,对他露出一个虚弱但温顺的笑容。
“是什么好东西?拿来看看吧,你知道的,我一看到那些漂亮的老物件,就什么疲劳都没了。”
这是我三年来,对他说过无数次的话。
他眼里的笑意瞬间加深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……如释重负。
呵,他怕的,是他的“工具”罢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