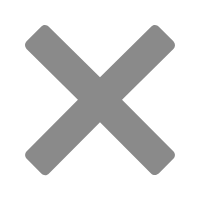-
日久见人心.
第二章
3
我自嘲地勾起嘴角,轻声说:“去吧,你的孩子需要你。”
他甚至没再回头看我一眼,仓皇离去,带起的风拂过我的脸。
我独自坐在黑暗中,没有开灯,也没有哭。
我知道,陆沉或许永远不会娶苏樱。但他会一次次地,因为那对孩子,被她叫走。
我调配过上千种香水,前调、中调、后调,层次分明,和谐统一。
可我的人生,却被硬生生塞进了一股不和谐的、廉价的杂味。
如果不离婚,我要忍受这种杂味多久?一辈子?
胃部传来熟悉的、针扎似的绞痛。
我蜷缩在沙发上,打开手机。
朋友圈里,苏樱发了一张照片。陆沉守在保温箱旁,侧脸憔悴,眉宇间是我从未见过的惊惶和紧张。
她配文:[有你在,就不怕。]
呵。
我让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,然后去了公司。
我亲手创立的香水品牌“Y”,如今是集团最赚钱的子公司之一。
HR总监看到我递交的辞职信,惊得差点打翻咖啡,“喻总,您要离职?陆总知道吗?”
我淡淡一笑,“他现在很忙。”
看着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同情,我知道,全公司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
回到西郊别墅,这里曾是我们为了清静,偶尔来住的地方。我的小型调香室还在这里。
收拾东西时,我在一本《香水史》里,翻到一张泛黄的便签。
是陆沉的字迹,青涩又张扬。
“言言,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看到。那时我们应该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了吧,一个像你,一个像我。我爱你,喻言。不管未来发生什么,都不许抛下我。”
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纸上,洇开了墨迹。
胃部猛地一阵剧痛,比任何一次都要猛烈。眼前一黑,我栽倒在地。
再醒来时,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。
“喻言!你到底想干什么!”陆沉的怒吼从听筒里传来,震得我耳朵发麻。他很少这样连名带姓地叫我。
“苏樱已经够小心翼翼、够委曲求全了!我都说过多少遍了,她不会影响到你!你为什么要给她发那些诅咒我孩子的恶毒短信?!”
我笑了。
笑得胃都在抽搐。
他甚至不问一句是不是我,就直接定了我的罪。
“说完了吗?”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他被我的反应噎了一下,气势弱了下去,“下周日,孩子满月宴,你必须出席。言言,别再耍性子了,好吗?”
“好。”
挂断电话,我望着窗外的漫天星辰,忽然觉得一切都了无生趣。
满月宴那天,我素颜到场。
在一众珠光宝气的宾客中,我像个格格不入的幽灵。
所有人都用那种夹杂着怜悯、好奇和幸灾乐祸的眼神看我。
宴会厅中央,苏樱穿着一身显眼的红色长裙,小鸟依人地偎在陆沉身边,笑得像个真正的女主人。
陆母看到我,皱着眉催促:“来了就去抱抱孩子,沾沾喜气。”
陆沉将那个女儿递到我面前,压低了声音,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,“言言,短信的事,我不追究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等过了今天,我会安排苏樱出国。孩子……孩子记在你名下。我知道你……”
他顿住了,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
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
当年我的实验室意外失火,他来找我,我为了把他推出去,吸入了有毒的化学气体,伤了根本。
医生说,我这辈子,很难再有自己的孩子了。
他曾抱着我发誓,这辈子我们两个就够了,他什么都不要,只要我。
如今,他却说:“这样,不是两全其美吗?”
我的心,像被那场大火又烧了一次,疼得快要无法呼吸。
就在这时,我怀里的女婴,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,小脸涨得通红,随即猛地喷出一口带血的奶沫。
“孩子怎么了!”有人失声尖叫。
4
苏樱像疯了一样扑过来,声音尖利得能划破玻璃:“喻言!你有什么冲我来!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!”
“啪!”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陆父亲手打的。
我被打得偏过头去,眼前金星乱冒,摔倒在地。脸颊火辣辣地疼,嘴里瞬间弥漫开一股铁锈味。
陆沉下意识地伸手,想要扶我。
就在他的指尖即将碰到我手臂的瞬间,地上的另一个孩子,那个男孩,也突然“哇”地一声,吐出一大口鲜血。
现场彻底乱了。
“陆总!”苏樱凄厉地尖叫着,像一块磁铁,硬生生挤进我们之间,“我们的儿子!快救救我们的儿子!”
陆沉伸向我的那只手,在半空中猛地一颤。
我清楚地看到,他眼中的挣扎和愧疚,被恐慌和心疼一点点吞噬。
最终,他慢慢地、慢慢地,收回了手。
转身,抱起了那个吐血的男孩。
医院走廊里,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。我像个游魂,站在这片纯白的世界里。
那份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,从我的大衣口袋里滑落,飘飘扬扬地掉在地上。
陆母眼尖,一个箭步上前捡起来,看清上面的字后,粗暴地甩回我脸上。
纸张的边缘划过我的脸颊,留下一道细微的刺痛。
她保养得宜的脸上满是淬了毒的厌恶,“你这个毒妇!这些年我们陆家哪点亏待你了?啊?阿沉为了你那个破香水,跟我们顶了多少次嘴,我们都忍了!现在你连两个无辜的孩子都容不下?”
“既然你这么想离,那就赶紧滚!别占着茅坑不拉屎,耽误我们阿沉!”
我沉默地弯腰,捡起那份沾了灰的协议。
ICU的门开了,陆沉走出来,眼睛熬得通红,“孩子……救回来了。”
他看着我,眼神陌生得像在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“喻言,这一次,你真的太过分了。”
我颤抖着,将离婚协议递到他面前,“我们……结束吧。”
他的瞳孔骤然收缩,死死地盯着我,“你确定?”
“我累了。”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,“我怕我再待下去,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……”
“好!好得很!”他猛地夺过协议,从口袋里掏出笔,狠狠签上自己的名字,然后将笔杆“啪”的一声摔在地上,断成了两截。
“喻言,如你所愿!”
回到我们曾经的婚房,那个被称为“世纪之家”的顶层公寓。
照顾我多年的许姨慌慌张张地迎上来,“太太!您……您的脸……”
我环顾四周。
客厅里我最爱的那架古董香水风琴,不见了。
墙上我们巨幅的婚纱照,消失了。
玄关柜上我从世界各地淘来的限量版香水瓶,也都不见了。
这个家,被清空了所有属于我的痕迹。
许姨搓着手,支支吾吾,“是……是苏小姐来养胎,说闻到香水味就头晕,陆先生就让人把……把东西都收进仓库了……”
门锁,开了。
陆沉带着苏樱走了进来。
苏樱靠在他怀里,看到我时,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,“喻总,您怎么来了?”
那语气,仿佛她才是这里的女主人。
“我的东西呢?”我的声音在发抖,死死地盯着陆沉。
陆沉冷笑一声,将苏樱往怀里更紧地带了带,“你都要离婚了,还管这些干什么?”
苏樱假惺惺地走过来,想拉我的手,“喻总,您别怪陆总,是我怀孕身子弱,怕磕碰到那些贵重的东西……”
“别碰我!”我像被火烫到一样,猛地甩开她的手。
她“啊”地惊呼一声,柔弱无骨地向后倒去。
陆沉眼疾手快地将她捞进怀里,紧张地上下检查,“没事吧?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”
我看着他们密不可分的样子,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我转身就走。
身后传来陆沉夹杂着怒气的声音:“喻言!你给我站住!”
我没有回头。
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此刻狼狈的样子。
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倾盆大雨,我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,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。
雨水冲刷着脸上的泪,冰冷刺骨。
不知走了多久,我被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堵在了一条阴暗的后巷。
“哟,这不是喻总吗?”为首的刀疤脸淫笑着逼近,“有人花钱,让我们哥几个好好‘伺候’你。”
他凑近了,用力嗅了一下,“真香啊。这科技新贵的过气老婆,就是不一样。”
我下意识地摸出手机,凭着本能拨出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。
电话很快被接通。
那头,传来的却是陆沉温柔得能滴出水的声音:“乖,别怕,只是噩梦,睡吧。”
是苏樱。
“陆沉!救我……”
“喻言,我现在没心情跟你玩这种把戏。”
电话被无情地挂断。
再打过去,已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。
冰凉的雨水混着绝望的泪水流进嘴角,咸得发苦。
“叫啊,你叫破喉咙,这里也不会有人来的!”
混混那只沾满油污的脏手,摸上了我的大衣领口,粗糙的指腹刮过我的锁骨。
我死死闭上眼睛,指甲掐进掌心,一片冰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