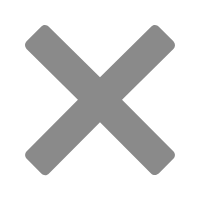-
替身两年被扫地出门,我让前夫给我下跪
第三章
我消失了整整一年。
萧景深大概以为,我拿着他那“慷慨”的一千万,找了个小地方,舔舐伤口,或者嫁给一个平庸的男人,庸庸碌碌地过完一生。
他太自以为是了。
他不知道,我离开萧家的第二天,就接到了一个来自瑞士银行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,一个言辞严谨的律师告诉我,我那对自称是普通商人的养父母,在我二十二岁生日这天,为我激活了一笔庞大的信托基金。
以及一个……足以撼动整个娱乐圈的人脉网络。
我那对早逝的养父母,原来从不是什么普通人。
他们曾是娱乐圈的幕后大佬,因为厌倦了资本的肮脏游戏,才金盆洗手,隐居起来,给了我一个看似平凡却充满爱的童年。
而他们留给我的,是我最强大的底牌。
是足以将萧景深和他那引以为傲的传媒帝国,踩在脚下的资本。
我没有动那笔钱,也没有联系那些人脉。
我要的,不是用资本碾压他。
那太便宜他了。
我要在他最引以为傲的领域,在他亲手建立的规则里,把他打得一败涂地。
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,他曾经弃如敝履的垃圾,一步步登上顶峰,成为他高攀不起的存在。
我要他后悔。
我要他痛苦。
我要他,为他曾经的所作所为,付出血的代价。
这一年,我改了名字,换了身份。
我叫“楚夜”。
我用最严苛的标准训练自己,声、台、形、表,每一项都做到极致。
我参加了无数个小成本网剧的试镜,从一个连镜头都找不到的龙套,演到有几句台词的女N号。
我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,磨掉身上所有属于“楚晚晚”的温顺,只留下属于“楚夜”的锋利。
直到我遇到了陆司寒。
陆司寒,国际知名导演,各大电影节的常客,出了名的眼光毒辣,脾气古怪。
他正在为他的新电影《囚鸟》寻找女主角。
一个外表纯洁如白鸽,内心却充满挣扎与毁灭欲的角色。
几乎所有一线女星都去试镜了,全被他骂了回来。
“我要的是一只渴望冲破牢笼的囚鸟,不是一群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。”他在片场发火的样子,第二天就上了热搜。
我去了。
没有经纪人,没有助理,一个人,穿着最简单的白T恤和牛仔裤。
轮到我时,我什么都没说,只是走到镜头前,给了他三个眼神。
第一个眼神,是初入囚笼的迷茫与恐惧。
第二个眼神,是久经折磨后的麻木与死寂。
第三个眼神,是在一片死寂中,突然燃起的,焚尽一切的疯狂与恨意。
最后一个眼神,我死死地盯着镜头,仿佛在透过它,看着那个毁了我一切的男人。
陆司寒当场拍板。
“就是她了。”
他甚至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