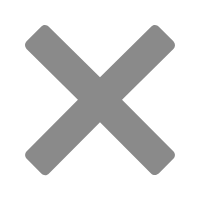-
颁奖礼上,我直播前夫的罪证
第五章
我跟林深签了合同。
没有发布会,没有官宣,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。
剧组很小,也很穷。
除了几个核心岗位是林深从海外带回来的班底,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新入行的年轻人。
拍摄地点就在我所在的小城,取景地是一家快要倒闭的纺织厂。
开机第一天,第一场戏,就是剧本里那场浴室独角戏。
导演是个一脸络腮胡的外国人,叫马丁,要求非常严苛。
为了追求真实,他要求我真摔。
冰冷的水泥地上,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
副导演有点不忍心:“马丁,要不还是借位吧?苏老师这身子骨……”
“不用。”我打断他,脱掉了外套,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,“按导演说的来。”
所有人都看着我。
我能感觉到他们目光里的同情、质疑、还有一丝看好戏的幸灾乐祸。
我不在乎。
这三年来,我受过的冷眼和屈辱,比这多得多。
马丁通过翻译对我喊:“准备好了吗?”
我冲他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
场记打板。
“Action!”
我按照剧情,跟饰演丈夫的男演员发生争执。他一耳光扇过来,我整个人被扇倒在地,头狠狠地磕在了水泥地上。
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
是真的疼。
疼得我眼冒金星,耳朵里嗡嗡作响。
但我没有停。
我挣扎着爬起来,一步一步,拖着“受伤”的身体,踉踉跄跄地走进临时搭建的浴室。
镜子里,我的脸颊高高肿起,嘴角渗出血丝,头发凌乱,眼神空洞。
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。
我打开水龙头,用冷水一遍遍地冲刷脸上的血迹和污垢。
然后,我拉开药箱,拿出棉签和消毒水,开始给自己上药。
棉签碰到伤口,身体因为疼痛而剧烈地颤抖。
眼泪,不受控制地往下掉。
一滴,一滴,砸在冰冷的水池里。
但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那不是委屈的哭,不是软弱的哭。
而是一种被逼到绝境的、麻木的、无声的控诉。
我的眼神,从最初的空洞,到慢慢聚焦。
最后,定格在镜子里那张伤痕累累却写满不甘的脸上。
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缓缓地,扯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
“Cut!”
马丁导演的声音,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他冲过来,激动地抓住我的肩膀,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英文。
旁边的翻译立刻跟上:“导演说,太棒了!苏,你就是他要找的女主角!你把那种从绝望里开出花来的感觉,演活了!”
剧组里,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。
那些原本看好戏的眼神,此刻都变成了敬佩和震撼。
我撑着洗手台,缓缓站直了身体。
腿肚子在打颤,后脑勺火辣辣地疼。
但我知道,我赌对了。
那个在镜头前会发光的苏清宁,回来了。